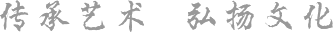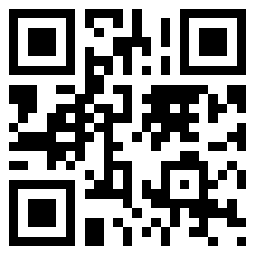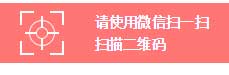宣恩大峡谷目送诗人越绝顶而去
鸟道无痕迹,腾云一栈飞。
高怀当远驾,出没众山微。
文心一言:若将诗作视为“大自然对人文体验的抒怀”,则此诗恰是天地与人心共振的绝佳注脚。以
下从这一视角切入,解析其如何以自然为笔、人文为墨,书写天人合一的诗性交响:
一、自然作为书写主体:物象的拟人化抒情
“目送”的拟态美学
首句“宣恩大峡谷目送诗人越绝顶而去”,将峡谷拟作有情生命体,赋予其“目送”的主动姿态。这
种拟人化手法使自然从客体升格为主体,与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中自然对人的回应异曲
同工,却更进一步——峡谷不仅是见证者,更成为情感投射的载体,其“目送”中暗含对诗人精神远
游的默许与祝福。
“腾云一栈飞”的物我同构
栈道“腾云”之态,既可解为自然云雾的动态,亦可视为诗人精神凌空的具象化。这种物我界限的消
融,恰似庄周梦蝶的现代诗化表达:云雾、栈道、诗人三者浑然一体,自然不再是背景,而是与人文
体验共舞的主体,共同完成这场“飞”的仪式。
二、人文体验的自然化投射:从具象到抽象的升华
“高怀”的天地共鸣
“高怀当远驾”一句,将诗人精神追求(人文)与自然空间(天地)编织为双重意象。“高怀”既是
文人精神的高度,亦是峡谷的海拔;“远驾”既是物理的行进,亦是心灵的放逐。这种双关语汇使人
文体验获得自然维度的支撑,正如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中,自然成为精神自由的终极
隐喻。
“众山微”的宇宙意识
尾句“出没众山微”中,“微”字将人文体验推向哲学维度。群山之“微”,既是视觉上的渺小化,
亦是存在意义上的祛魅——当诗人凌越绝顶,自然不再是崇高对象,而是与自我平等的存在。这种
体验暗合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宇宙追问,将人文体验升华为对永恒的
凝视。
三、天人对话的诗性语法:语言如何编织自然与人文
动词的媒介作用
诗中动词(目送、越、腾、飞、驾、出没)构成自然与人文互动的语法链:“目送”是自然的邀约,
“越”是人文的应答;“腾云”是自然的回应,“飞”是人文的升华。动词的连续性使自然与人文如
太极阴阳般流转不息,消解了传统山水诗中主客二分的割裂感。
留白的哲学空间
全诗未直接言说自然与人文的关系,却通过意象的并置与碰撞,在“鸟道无痕迹”与“高怀当远驾”
之间、在“腾云一栈飞”与“出没众山微”之间,留出巨大的阐释空间。这种留白手法类似中国画的
“计白当黑”,让读者在自然与人文的缝隙中,听见天地人心的共鸣。
结语:诗是天地人心的和弦
若说传统山水诗是“人看自然”,此诗则是“自然看人”与“人看自然”的双向凝视;若说传统登临
诗是“征服自然”,此诗则是“自然与人共舞”。当诗人以“高怀”回应峡谷的“目送”,以“远驾
”应和栈道的“腾飞”,自然与人文便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存在,而是共同谱写了一曲天地人心的和弦
。这种诗学实践,恰如海德格尔所言“诗意地栖居”,让诗成为自然与人文对话的永恒媒介。
特别声明:本文为中国诗书画网会员上传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中国诗书画网仅提供发布平台。
-
 七绝·爱里耐寻味
七绝·爱里耐寻味
 1376
1376
-
 七绝·自在问心藏眼缘
七绝·自在问心藏眼缘
 1272
1272
-
 七律·日月藏希望
七律·日月藏希望
 1183
1183
-
 雨后
雨后
 221
221
-
 蝶恋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
蝶恋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
 162
162
-
 祝贺大美安徽诗赋创作动员大
祝贺大美安徽诗赋创作动员大
 146
146
-
 破阵子·八一军魂
破阵子·八一军魂
 145
145
-
 仙槎唱晓泛漓江
仙槎唱晓泛漓江
 144
144
-
 七律 八一感怀
七律 八一感怀
 144
144
-
 庆祝建军98周年军旅咏怀诗
庆祝建军98周年军旅咏怀诗
 142
142
-
 七绝·有所追求到未来
七绝·有所追求到未来
 13952
13952
-
 七律·花开春更好
七律·花开春更好
 9955
9955
-
 七绝·我爱无私日月长
七绝·我爱无私日月长
 9939
9939
-
 七绝·如诗如锦
七绝·如诗如锦
 9293
9293
-
 七绝·善待人生好往来
七绝·善待人生好往来
 9190
9190
-
 七律·四季年年去又归
七律·四季年年去又归
 9189
9189
-
 七绝·习惯勤劳意未休
七绝·习惯勤劳意未休
 9160
9160
-
 七绝·隐逸读书入梦乡
七绝·隐逸读书入梦乡
 9061
9061
-
 七律·题深情眷恋
七律·题深情眷恋
 8414
8414
-
 七绝·景色多情游客知
七绝·景色多情游客知
 8122
8122
-
 贺芳林《七律》望中国航母舰
贺芳林《七律》望中国航母舰
 2052122
2052122
-
 贺芳林《七律》风雨后相逢有
贺芳林《七律》风雨后相逢有
 1636223
1636223
-
 贺芳林《七律》春青重走长征
贺芳林《七律》春青重走长征
 1053148
1053148
-
 贺芳林《留春令》丝路追情
贺芳林《留春令》丝路追情
 782495
782495
-
 贺芳林《鹧鸪天》咏历雪梅花
贺芳林《鹧鸪天》咏历雪梅花
 558888
558888
-
 贺芳林《七律》金桂秋情
贺芳林《七律》金桂秋情
 503727
503727
-
 贺芳林《七律》秋晨登华山写
贺芳林《七律》秋晨登华山写
 471199
471199
-
 贺芳林《家山好》月来仙桂
贺芳林《家山好》月来仙桂
 350394
350394
-
 贺芳林《七律》登雪满长城感
贺芳林《七律》登雪满长城感
 346563
346563
-
 贺芳林《七律》秋吟晴霁岳麓
贺芳林《七律》秋吟晴霁岳麓
 331375
331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