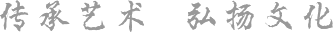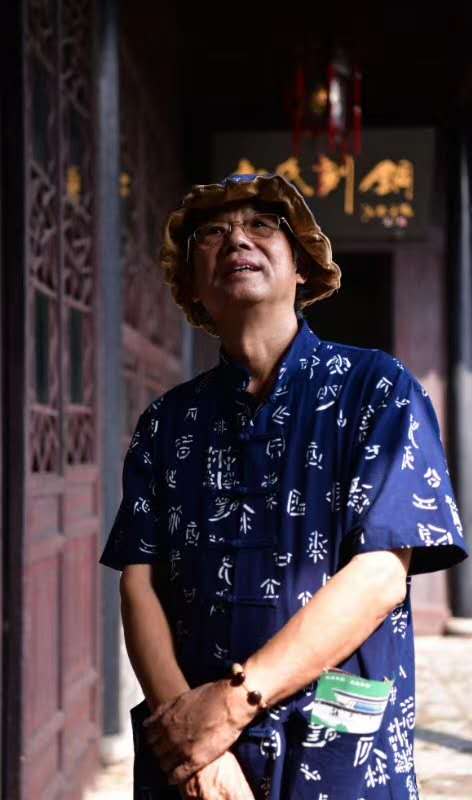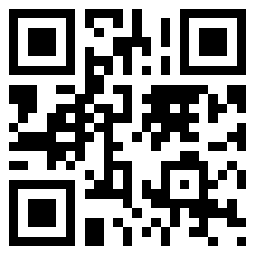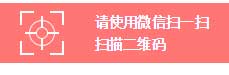二十四
正当夏先生犯愁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马猴“负荆请罪”来了。
第一次劫掠,马猴(好像)并不知情。当听到对“战况”的汇报后,尤其了解了“大桥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是夏五云夏先生和“投资者”是张镇芳张督军时,他做出了一个令一班弟兄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的决定:把好不容易带回的“战果”退回去,且他本人亲自去向夏先生道歉。
谁说流水不会向西、浪子不会回头呢?
而且马先生是坐着等来的。
一切都出于马猴微妙的心理。
一个土匪头子与一个私塾先生相见,我们不知道它真实的细节。有些尴尬?还是别有情调?还是像吴先生说的,两人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把盏品茗呢?
不管怎样,工程又启动了。
我们只好这样理解:“德高望重”这个词确实有引导事物往美好方向转化的力量。
二十五
两座桥都建好了。夏先生成了当地一个“伟大”的人物。但马猴建立在美妙心理之上与夏先生达成的默契于自己一方不仅没有实现,还为此丢掉了性命。
他帮助——这是委婉的说法,只是不骚扰而已——夏先生,目的是:他希望政府“招安”自己,托夏先生做一个转达,并让德高望重的夏先生做一个担保。这与《水浒》中的情节类似。
这是好事啊。夏先生一口应承并积极地为之奔走。
“改恶从善,好!我们欢迎他来!”“领导”态度明确地说。
但人心叵测,夏先生哪里知道他以真诚换来的却是一个包装漂亮的欺诈。因为,官府不相信土匪,就像神仙不相信魔鬼一样,尽管有时他们的品质更为低下。而且,许多人不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官府对土匪与百姓的处置,无论怎么都不为过。即使是欺诈,也是“阳谋”。
结果,马猴自投罗网。
事与愿违,夏先生成了“帮凶”。
马猴的弟兄们闻之,决心与“人民”对抗到底。只可怜了无辜的百姓。
所幸的是,夏先生没有遭到报复。
倘若有,就是来自内心的自责。
二十六
我们在直瀔头集没有停留,驱车上了返回县城的公路。
当路过一个叫夏营的村子时,吴先生向我们又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若不是车子奔驰的速度和太阳下落的速度都太快,每一个村子他都会给我们讲出一个离奇的故事来。
这个故事的次要人物叫夏权如(或许是夏全如)。他的祖父是夏营人,在莲池集上开了一个小旅店,大概是早得了“顾客就是上帝”这一秘籍,经营得还算不错。有一年,从山东兖州来了父女二人,在莲池集上卖艺,晚上就住在夏家旅店里。后来,父亲不幸染病身亡。临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了夏老板。顺理成章,这女子就成了夏老板的儿媳——两年后,生下了夏权如。
这女子绝非一般卖艺之人,而是一位功夫十分了得的“红拂女”。夏权如自幼随母亲习武,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武师。
除了一身万夫莫当的武功外,夏权如还是一位非常讲究武德的人。
夏权如以开馆授徒为业。有一年,他在今项城柳行,受到了挑战。对方是一个会点“三脚猫”功夫的“牛二”。
整个情景与《水浒传》中洪教头与林教头相遇一般:
“我只是混碗饭吃,还请仁兄高抬贵手!”夏权如不住地打拱作揖。
但“牛二”就是牛,就是二,不依不饶。
“那这样”,第三天头上,夏武师被逼得无奈,说,“我明天让我的一个徒弟与你走两步吧!”
“你徒弟呢?”第二天,“牛二”问。
“徒弟?今个不巧,他家里有点事。”夏武师思量着,能尽量避免还是避免。
“那好,我再给你一天的时间。要么他来比,要么你接手。”
没办法,夏权如次日只好叫上了大徒弟刘子元。
那“牛二”与刘子元在众目睽睽之下,拉开架势,开始过招。
结果毫无意外。只三招四式,“牛二”已露出破绽,刘子元一个饿虎掏心,铁锤一般的拳头就砸在对手的胸口,随着“喀嚓”一声,“牛二”就倒在了地上。
原来,这“牛二”有备而来——他在上衣下面用布条绑了一块犁铧面子。
二十七
前面提到,夏权如是这个故事的次要人物。我这样说,并不表明除了与“牛二”那点小事外,再无传奇的经历可言。只是你得给吴先生机会。否则,我不得不凭空杜撰了。
现在且讲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范浮。
范浮——或者范服或者范伏,反正就这个音——是夏权如的另一个徒弟。因为性格阴鸷,他被夏权如提前给毕了业。范浮怀恨在心,瞅机会准备教训一下老师,让他知道当初的决定是多么草率。
一天,范浮给老师捎信,邀请他到家叙旧。夏武师了解自己的学生,不愿得罪他,就如期而至。
两人在院子里隔着石桌对饮。
“师傅,”范浮问,“如果像咱们俩这样坐着,对方突然给你一刀怎么办?”
“那还不简单,躲过不就是了。”
“我叫你躲!”话音未落,范浮突然从背后抽出一把“刀”,照着夏权如的头上砍了下来。
夏权如的功夫果然十分了得,随着“噌”地一声,身子已退到一丈开外。
大门不知什么时候已被范浮锁上了。夏权如跑到墙边,纵身一跃,翻墙而去。那范浮不愧是夏权如的学生,也“噌噌”两下,越墙而追。
但村外一条小河把二人隔开了。对岸,老师向学生挥了挥手说:“范浮,回去吧。以后好好做人。切不可随便伤害无辜。”
……
这话是他改邪归正的良药,但范浮把它掷在地上并踩上了一脚。
范浮的阴鸷表现在:如果一个人冒犯了他,他就会报以微笑。但是,这“微笑”不是天使的祝福,而是魔鬼的诅咒。因为,凡是得到范浮“微笑”的人,结果只有一样:死。
范浮的“刀”与众不同,刀头带一个钩,叫做钩镰子。范浮是走路背着,睡觉枕着,随时都在为它寻找一个噬血的机会。
一次,他本家一位老叔,受了风寒,咳嗽不止。不想他的神经系统毫不知趣,在碰上范浮的时候,不能将声音及时控制。
但这位老叔的意识还算机灵,在看见范浮微笑的那一瞬间,使主人跪在了地上。
他为自己感到庆幸。
据说,这是范浮鲜花似的“微笑”唯一没有“结果”的一次。
二十八
人是复杂的。
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在于他将心中的善与恶做怎样的平衡。一个好人未必没有做恶的想法,一个坏人未必没有行善的可能。
爱以“微笑”对他人判处死刑的范浮,也有过“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我之所以把这四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它有一个出人想象的后果。
在莲池某一个村子——请理解我回避它真实的名字——有一户人家,媳妇刚过门,就被邻里也是一个“魔鬼”强暴,后来,女儿也不能幸免。忍无可忍之下,这家老太太在“高人”指点下去找“魔鬼”的祖师爷——范浮。
老太太到了范浮所在的村庄,见一个人蹲在路口的一个石磙上吸旱烟,就过去打听。
听了老太太的叙述,这人说:“你说的是实话啊,还是瞎话啊?我听说范浮的脾气有点怪,若你有一句瞎话,你全家可就没命了。”
“我说的若有一句瞎话,叫他杀俺全家。”老太太忙跪倒在地诅咒说。
“好!你回去吧。见了我就等于见了范浮。”这人又嘱咐说,“你回去后,在你家大门外燃一根麻秸火,在那一家大门外的树上系一个布条。”
老太太叩了头,半信半疑地走了。
第二天,一个惊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附近的村庄:一家七口人被杀了八口——一个无辜的亲戚,也为他们的儿子抵了罪。
人命关天。案件惊动了槐坊镇警察总局(槐坊镇是一个特别镇,在总局之下设三个分局,分别管辖属于沈、项、淮三县的区域)。
在警察验尸时,范浮也在现场围观,并像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提出了绝对具有参考价值的看法:“刀口都一样,应该是一人所为。”
但案没破,尽管省警察厅也派人来了。
这不是警察同志的错,错的是那时的刑侦技术——你想啊,连个DNA也无法鉴定。除此,没别的解释。
二十九
那个连邻里家的女人也不放过的“魔鬼”,没想到他的祖师爷找上门来,遭到了灭门绝户的“教训”。这应了那句话:上帝想惩罚一个人,会先让他疯狂。
对范浮,上帝也没有过多的眷顾,尽管他有过“伸张正义”的行为。
在槐店东南如岳阁、贾寨一带,数百年来就有逢年过节燃放焰火的习俗。在娱乐单调的年代,这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有一年贾寨放焰火,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爱好的范浮也去了。
返回时,有一户人家的狗没有认出他。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它不够礼貌的狂吠,使主人丢掉了性命。
那老先生,从后面故事情节的发展推测,也是一个有所依仗的人,在平时与他的狗相比绝对多得多的智慧,此时显得非常捉襟见肘。这句话复杂了点,没有范浮说得简单:“狗不懂事,人也不懂事吗?”
魔鬼有时候也是讲点道理的。
老先生为自己的失误付出了代价,以自己的头颅验证了范浮钩镰子的厉害。
三十
在范浮的意识里,只有他对别人“微笑”的份,没有别人对他“呲牙”的理。他不知道,如果他所在的区域扩大一些,这句话可能就要颠倒一下。
老先生的死,惹怒了一个人——汪精卫部下的一个师长——符子建(符子建是我给他起的一个化名,因为他就是本地人,我还是回避一下好)。老先生是符师长的表叔。
我们不清楚这符师长是否上过抗战前线,但为这件事,他回到了故乡。
“范浮,”符师长找到了范浮,说,“我虽然带着枪,但我不用。你也不要用你的钩镰子。来吧,咱们过几招。”
范浮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把钩镰子交给了旁边的一个弟兄。
二人拳来掌往,打了四十个回,结果范浮落荒而逃。
符师长的职位不是白混的。
范浮对村子虽然熟悉,但仓皇之间跑进了一位老太太家里,躲在一间屋子的床下,被随后追上来的符师长“砰砰”两枪打了个正准。
范浮为他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也偿还了一生的罪孽。
只是,符师长的结局比范浮“美满”不了哪里去——他在解放战争中,被人从城墙上抛下,摔死了。
三十一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有一定道理的。”一生经历坎坷的吴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说:“说到范浮,不能不说另外一个人——王老得。”
王老得本有一个非常斯文的名字,但他以绰号行世。在沈项一带,至今有人给一个姓王的同事或伙计起外号时,最容易联想到的还是这三个字。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王老得与范浮不同。范浮靠的是武,但把钩链子别在裤腰上的时候,也把脑袋别在那里了。王老得凭的是文,凭的是智慧,凭的是四两拨千斤的能力。若说二人没有共同点也不对。他们的共同点就一个字:恶。
俗话说,勾头老婆仰头汉,不赚便宜就不算。王老得就是一个走路昂首挺胸的人。在他看来,除了神仙,皇帝老儿也未必有自己过得自在。
他是讼师。
讼师——就是现在的律师——在一个十里八村也找不出几个识字的人的年代,这是除了官府以外最高尚的职业了。
使他得意忘形的并非归因于家有良田几十亩,而在于他在为人诉讼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诸如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之类创造的快感。
王老得与他邻居的地界与众不同——他的邻居需要让出三尺才行,否则三丈以内的收成全部包赔他恐怕都是一件便宜的事。
莲池南有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整天东游西逛,不务正业,还有点“二愣子”性格。有一天,不知因为什么事,他与他爹争吵了起来。李老汉气愤不过,抬手扇了他两耳光。不想儿子非常具有现在人平等公正的思想,一拳打过去,李老汉的两颗门牙就血淋淋下岗了。
三十二
是可忍,孰不可忍?李老汉一怒之下将儿子告到了县衙。
儿子感觉事情严重了。他听说,像这种致自己老子“二级伤残”的案子,是要判坐牢的——那滋味可不好受。
经人指点,他找到了王老得。
“不是什么事”,王老得对忐忑不安的二愣子说。
“你爹知道你上这来吗?”
“知道。”
“去到院子里抱劈柴来,在屋里生一堆火。”这六月天烤什么火啊?二愣子不明就里,
但他不敢不按王老得的吩咐去做。
“穿上我这件皮袄。”王老得找出一件翻毛羊皮大袄来。
二愣子更糊涂了。
一个时辰后,二愣子仿佛一只练习潜水的老母鸡刚上岸。
“把肩膀扒出来。”到院子里溜达了一圈的王老得说。
一个平时不愿意担当的肩膀,被一个能将死蛤蟆说出尿来、能把死马说得尥蹶子的牙齿咬下了一排深深的牙印。
县衙大堂上,盛气凌人智慧未比凌人的县长问:“李XX,你儿子说,你的两颗门牙是你咬他的肩膀时,他往后一退,你挣掉的。”
“青天大老爷,你想,他力气又大,个头又高,会老老实实地坐着让我咬?”
“那他肩膀上的牙印不会是他自己咬出来的吧?”
“大老爷,你有所不知,那都是王老得的点子。”
“王老得的点子?”
“我儿子去找王老得,他前脚走,我后脚跟。我偷偷地趴在他家窗户外边,看得一清二楚!”
“你看到了什么?又听到了什么?”
“他们在屋里生了一大堆火,我儿子穿着皮袄坐在旁边烤……”
“不要再说了!你儿子说你老糊涂了,我看一点不假!退堂!”
二愣子如释重负。只老汉又羞又气,胸口如压了一块石头,回家就卧床不起,不出半月,竟然一瞑不视。
将智慧用于行善的人,是天使;将智慧用于作恶的人,一定是魔鬼。王老得将智慧用错了地方。
三十三
这只是王老得无数得意之作中的一个。另一个,在为他带来了无限的“荣耀”、使他闻名遐迩的同时,也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窦姓是槐坊镇上的大姓——有一个窦举人(如果我知道得更详细的话,我会把他的简历写几句),有一天去街上散步,被一篮子个大色鲜的石榴吸引了眼珠。
“老表,咋卖的?”,窦举人一边拿起一个石榴端详,一边问小伙子。
“一个三文钱。”
“俩多钱?”
“六文。”
“五文行吗?我今个就带五文。”
“不卖。”
“小伙子,你做生意咋这样啊?!你连窦举人都不认识?”旁边有人过来说。
“对啊!窦举人又不是没有钱。他也不是专门出来买东西的。要不,别说你这一篮子石榴,就是一车,窦举人也买得起。”另一个也围上来帮助“撮合”。
“一个三文,两个六文,少了不卖!”小伙子在没吃拳脚前不认吃亏。
“你口气这么硬啊?以后还来不来槐坊镇啊?”
“怎么?槐坊镇是你们开的?”
小伙子从话里没明白的,随即从劈头盖脸的拳脚中明白了。
结果,小伙子得了五文钱,窦举人拿走了两个石榴。
但这不是最后的结果。
三十四
“你怎么不说你的掌柜是我啊?”王老得对跟了自己多年没长一点智慧的小伙子呵斥说。
“我说了。我不说还好,一说打得更狠!”小伙子的脸上除了血污满是委屈。
“好一个窦举人,真是欺人太甚!”王老得被激怒了。
由此可见,小伙子跟着王老得并没有白混——他不是一个省油的灯。社会往往因为这种人的存在而热闹了许多。
窦举人被告上了公堂,为他出门的时候少带了一文钱。
故事一开始说,窦举人出自大户。大户自然有大户的背景,有大户的能量。于是案子从县转到了市(当时没这种称呼,估计是专区或者公署),又从市转到了省。
省城开封,那可不是一般老百姓去的地方。但王老得和窦举人可以,怎么说他们也是地方名流啊。
案子判决了。窦举人向小伙子当庭磕了三个头,作为对他有失身份的言行的惩罚。
“法官,他这样陪个礼道个歉就算完了?”
刚直起身、尚羞愧难当的窦举人听完王老得的话,几乎要晕过去了。
“我们为啥打官司啊?他还欠我们一文铜钱呢!”
法官哭笑不得,只好再判窦举人掏出那该死的一文钱。
三十五
窦举人掏出一枚铜钱的那一刻,王老得心情之激动,不亚于大唐时期那个屡次落第的诗人孟郊忽然在皇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王老得乘着马车回到了沈丘,悦耳的铃铛声如花一样洒落了一路……
从此,王老得的脸扬得就与天空平行了。
刻骨铭心地领略了“欺人太甚”一词的窦举人也回到了家。与王老得不同的是,他一病不起。
窦举人引起的故事结束了。而王老得还活在世上,继续他“创意”不断和“传奇”不断的事业。
他甚至把那位没有足够地偏袒他且于两年前已调到了郾城的县长也告掉了。
但人世间的事往往难以预料,就像一枚种子落在泥土中,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发不出芽,结不出果实,甚至会腐烂掉,但也有一种可能:在谁都忘却谁也不在意的某一天,它又破土而出,长成一棵大树并结满了果实——尽管这些果实未比都是甜的。
我想说的是,王老得已为他的最终结局埋下了种子。
这结局出乎他的想象——一个人得意忘形的时候,智慧总是慢一拍。
某一天,有两个人驾着一辆豪华的马车来了——请他去柘城代理一个状子。
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不是名扬天下的人物是不足以当之的。
王老得换了一身体面的衣服,对他的家人挥了挥手,登上了马车……
但他永远也没有回来。
特别声明:本文为中国诗书画网会员上传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中国诗书画网仅提供发布平台。
- 游客
- ¥2.00
- 2021-02-13
- 露白
- ¥1.00
- 2020-03-26
- 露白
- ¥2.00
- 2020-03-23
- 游客
- ¥1.00
- 2019-12-22
- 游客
- ¥1.00
- 2019-12-22
- 游客
- ¥1.00
- 2019-12-21
- 游客
- ¥5.00
- 2019-12-21
- 游客
- ¥2.00
- 2019-12-21
- 贺芳林
- ¥5.00
- 2019-12-21
- 游客
- ¥1.00
- 2019-12-19
- 游客
- ¥1.00
- 2019-12-19
- 游客
- ¥1.00
- 2019-12-16
-
 七律·仁义礼智信
七律·仁义礼智信
 8443
8443
-
 七绝·自驾游春三世间
七绝·自驾游春三世间
 8426
8426
-
 七绝·悄然梦醒是新吾
七绝·悄然梦醒是新吾
 8353
8353
-
 七绝·不屑红尘把爱抛
七绝·不屑红尘把爱抛
 8352
8352
-
 七绝·你我欣然如凤仪
七绝·你我欣然如凤仪
 8341
8341
-
 七绝·爱得情自愿
七绝·爱得情自愿
 8320
8320
-
 七绝·满目倾情信爱人
七绝·满目倾情信爱人
 8304
8304
-
 七绝·致敬顾浩先生
七绝·致敬顾浩先生
 8266
8266
-
 七绝·情感无声意味长
七绝·情感无声意味长
 8255
8255
-
 七绝·我爱如风入洞天
七绝·我爱如风入洞天
 8241
8241
-
 贺芳林《七律》望中国航母舰
贺芳林《七律》望中国航母舰
 2030305
2030305
-
 贺芳林《七律》风雨后相逢有
贺芳林《七律》风雨后相逢有
 1634343
1634343
-
 贺芳林《七律》春青重走长征
贺芳林《七律》春青重走长征
 1050459
1050459
-
 贺芳林《留春令》丝路追情
贺芳林《留春令》丝路追情
 774560
774560
-
 贺芳林《鹧鸪天》咏历雪梅花
贺芳林《鹧鸪天》咏历雪梅花
 558556
558556
-
 贺芳林《七律》金桂秋情
贺芳林《七律》金桂秋情
 503407
503407
-
 贺芳林《七律》秋晨登华山写
贺芳林《七律》秋晨登华山写
 470849
470849
-
 贺芳林《家山好》月来仙桂
贺芳林《家山好》月来仙桂
 350142
350142
-
 贺芳林《七律》秋吟晴霁岳麓
贺芳林《七律》秋吟晴霁岳麓
 331104
331104
-
 贺芳林《七律》登雪满长城感
贺芳林《七律》登雪满长城感
 322373
322373